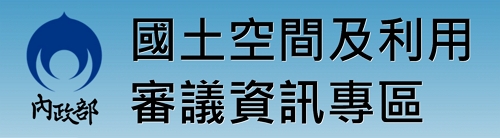在這樣乾冷的冬日裡,就連夢境,也都是乾冷的。
在這樣乾冷的冬日裡,就連夢境,也都是乾冷的。昨夜竟然夢見自己重新踏足在那年元旦的北坑溪古道之上,仰視雪山山脈的巍峨高聳、俯瞰大安溪谷的溝壑深邃,視線停格在楓葉渲染橙紅的日向稜線。
只消風一起,葉子便危危顫顫地在樹梢上興起一陣手舞足蹈;而當風再吹起,整個樹林,彷彿都隨著風的吟唱,陶然晃漾起來。紅葉轉著圈圈,飄落如天女散花,旋即淋了我們一身的葉子雨。
夢境醒轉,心頭猛然一驚。
那一年的北坑溪,白晝籠罩著暖暖的冬陽,足下輕輕踢著失去水分、自然乾燥的捲曲落葉,發出嘰嘰茲茲的季節性脆響。行經崩壞的路段,步伐稍用些力,就揚起不少塵霧。行進間的我,不時舔舐著乾裂的嘴唇,鼻腔則隨時都隱伏著一股期盼滋潤的渴望。
 記憶中的北坑溪古道,始終是這樣乾燥而輕盈,空氣清冷得彷彿可以...直達天聽。
記憶中的北坑溪古道,始終是這樣乾燥而輕盈,空氣清冷得彷彿可以...直達天聽。白晝被太陽烘暖的空氣,在入夜之後因輻射冷卻效應全數釋回,散逸於宇宙星河間的浩瀚,天寒地凍得必須縮躲在帳棚中炊煮兼取暖;有時披著睡袋,從樹林的間隙遙望星月交輝,有時則猶豫著遲遲不敢探頭。
北坑溪的記憶,在我心中似乎也代表著某種無可取代的意象。那年,所知尚甚為貧乏,就闖進了北坑溪古道;帶著無數的驚喜與嘆息離開。
曾經一個貪看滿山楓紅的白晝,加之以步步為營通過驚險斷崖的時間延誤,我們直至日落時,方抵預定的宿營地。就著淡淡的月色,徒步往返一小時遠的水源處取水。疾行的呼息,和著步伐扣弄石塊的輕響,與微弱的溪谷水聲遙相呼應。
 猶記得我們停歇在一處蓊鬱的森林間,放下背包研讀著地圖與記錄。森涼的空氣,揉合了山林獨特的氣味,兼以歷史冥想的餘韻,滲透著汗水浸濕的皮膚,直抵胸臆。順著葉隙跌落的斑斑陽光,卻及時烙了我們一身暖意。
猶記得我們停歇在一處蓊鬱的森林間,放下背包研讀著地圖與記錄。森涼的空氣,揉合了山林獨特的氣味,兼以歷史冥想的餘韻,滲透著汗水浸濕的皮膚,直抵胸臆。順著葉隙跌落的斑斑陽光,卻及時烙了我們一身暖意。一個紮營在雪見的夜晚,滿月在子夜時分順著林間的天井來訪,將帳篷輝映得如同點亮的燈籠般透著光明和溫暖。輕輕拉開帳篷的門,仰望著樹冠上層,只見葉片上全棲滿了清亮的月光,宛如一片裝飾華麗的聖誕樹林;半夢半醒的我,還一度錯以為自己置身在停滿螢火蟲的樹林子裡呢!
那時,我們對古道的踏查還不夠成熟,部分懷疑是日據時代駐在所的疊石,應該是昔日原住民的墾地與家屋的殘跡。然而,北坑溪如詩如畫的冬日、北坑溪處處生機的展演,卻是讓人低迴再三的山林面貌。
古道上結了滿樹紅果實的山桐子,是鳥群覓食兼絮呱的場域;日向稜線上,隨著正午的烈日火紅延燒的整片楓香樹海;雪見溪谷入夜以後山羌此起彼落的鳴吠; 幸原附近碎石坡上,與一群黃山雀近距離共享野生梅花盛放的芬芳;又及,清晨時分藍色調中的雪見溪滑瀑,始終深深地烙印心坎。
我曾經隨性坐在粗壯的血藤天造地設的天然盪鞦韆上頭,像個頑皮的孩子;仰首是一株瘦而高的蓪草,張開了大手掌狀的葉片,向著天頂爬行。而前幾日行經萩岡斷崖,貼著破碎山壁邊緣命懸一線的戒慎恐懼,早已拋諸腦後。
寒流來後的第二天,林道上的空氣真是冷冽。我們卻置身在空曠處,環視著視野裡頭清晰而粗獷的稜線起伏,看雲隨著氣流的噴湧將山景抹上一層霧白,守候著太陽緩緩下沉時的天際晚霞。
林道上的界碑 目送夕陽西下時分遠去的司馬限林道,山林的沉靜、大自然裡生命的競爭與和諧、群鳥齊鳴的無邊天籟、萬物間微妙的平衡、自成秩序,就此遠去。
這種種的美,真是讓人屏息以待啊!


夢醒之後,望見白色的窗簾外頭一抹橙汁色的陽光,恍如在北坑溪醒來的每一個清晨。我靜靜地坐起好一會兒,回想著屬於北坑溪冬日的種種美麗與豐饒。
「再看一次北坑溪的幻燈片吧!」我提出這樣的請求。只因在乾冷的冬日裡,我又夢見自己回到了北坑溪,置身在冬日陽光下的森林氛圍。 究竟有沒有一種方法,可以重現停留在我心中的那一片永恆呢?
總覺得在看到、決定按下快門的當時,是最美、也最感動的了;用幻燈機打出來的影像雖然也很美,可是那種感動就差了一點;變成影像檔在電腦上播放,似乎又 再差了一些。有些幻燈片可以用光呈現,卻始終沒有辦法掃成數位影像檔。失落的那些部分,恐怕只能靠朦朧的記憶與內心的光亮去彌補了。